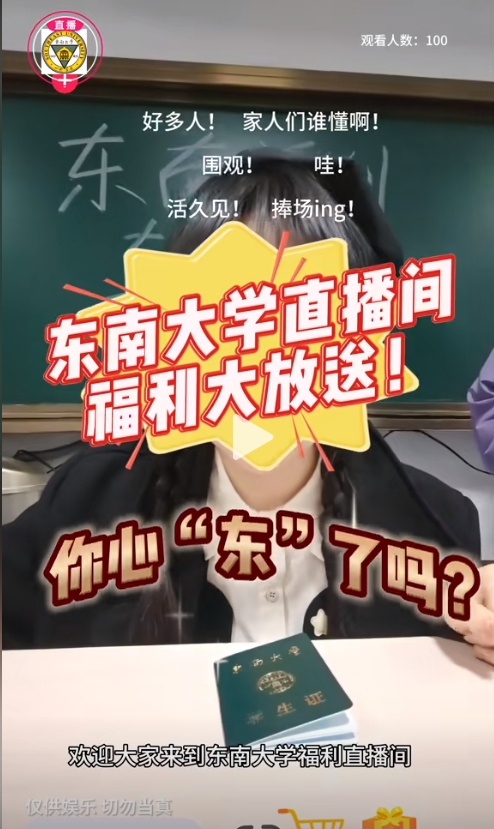南极洲是地球上最遥远、最孤独的大陆。自从1840年人类发现南极大陆以来,数以千计的探险家和科考人员前赴后继地奔赴南极,试图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如今,在南极的科考舞台上,也出现了东大人的身影。
2007年,我校2005届艺术学院毕业生曹硕伟校友参与第24次南极科考时,第一次让东南大学的校旗在南极上空飘扬。今年元月,我校自动化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魏海坤教授作为“南极冰穹A科考支撑平台”的现场执行人参加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使我校研制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极地天文科考支撑平台在南极成功运行,实现了现场无人值守、坐在南京遥控南极科考的梦想。
生命代价的南极科考支撑平台
南极大陆拥有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到目前已有近三十个国家相继在南极建立了一百多个科学考察基地。这些众多的考察站,根据其功能大体可分为:常年科学考察站、夏季科学考察站、无人自动观测站三类。
位于南极东南极中心的 Dome A(冰穹A)被命名为地球上的“不可接近之极”。它作为南极冰盖冰芯钻探仅存的最后一个理想地点和世界上雪冰现代气候环境观测、大气与气象观测等独一无二的“科学观测站”,在科学上的意义是地球上其他任何科学观测站所无法代替的。2009年1月27日,我国在南极内陆“冰盖之巅” Dome A成功建立了中国第三个南极科学考察站——昆仑站。巍然矗立的中国昆仑站是目前南极所有科学考察站中海拔最高的一个。由于昆仑站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它在起步阶段还只能建成无人值守自动观测站。
2007年,来自我国紫金山天文台和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朱镇熹和周旭在冰穹A搭建了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大学为主研制的一套天文科考支撑平台——PLATO,并陆续安装了天文望远镜等仪器。这些观测数据通过卫星传回设在澳大利亚新兰威尔士州立大学的数据中心,该大学长年派人24小时值班,随时监控温度控制状态。当时双方约定,数据共享。但几年下来,我国科学家越发感觉被人“卡脖子”。虽然我国为平台建设承担了不少费用,但要获取数据,必须向澳方提出要求,获得批准后对方才会转发一份数据,有关我国南极昆仑站的一些敏感数据仍然拿不到。在很多场合,澳方发表论文时甚至不再提及中国。
国内天文界研究人员决心携手改变这一现状。2009年9月,东南大学和紫金山天文台签订合同,计划在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中安装自己的能够为各类科考仪器提供能源、控制、数据存储、通讯等功能的天文科考智能支撑平台。在校领导的鼎力支持下,我校充分利用学校的多学科优势,迅速组建了由空间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郝英立教授领衔的项目组,承担了“南极冰穹A科考支撑平台”的研制任务。该项目组成员包括空间研究院的郝英立、邱实、方仕雄,自动化学院的魏海坤、张侃健、朱蔚萍,能源与环境学院的张辉、刘西锤,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王炎,电气工程学院的赵剑锋、金龙、黄云凯,以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我校就读的博士后唐敢等13位专家、教授。他们分别承担现场主控系统、发电系统、结构与温控系统、数据存储系统、通信及国内监控系统等,利用这些系统提供南极天文望远镜等观测设备运行所需的电力,并对天文设备进行实时监测、遥控及数据通讯。澳大利亚开发这样的平台已经走过八年的历程,而项目组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研发出科考支撑平台,并且很快就要送到南极去承受实战的考验,不仅难度很高,而且压力更大,出现任何差错都会给科考工作带来重大损失。在郝英立教授统筹下,项目组克服了时间紧、任务急的困难,进展迅速,多次获得项目合作方紫金山天文台的高度赞扬。
在平台项目研制过程中,我校分管科研工作的沈炯副校长和科技处处长李建清、张晓兵副处长等十分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并给予了大力支持。三位领导经常参加项目组的例会,沈校长还结合自己丰富的工程经验给项目组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张晓兵副处长亲自为项目寻找适合的航空燃油和模拟低温环境的冷库……。经过大家群策群力,2010年5月,“南极冰穹A科考支撑平台”进入组装联调测试阶段,并于6月23日运往西藏羊八井进行高原模拟环境下的综合测试。7月6日,郝英立带领项目组成员魏海坤、黄云凯、张侃健、邱实、方仕雄,朱蔚萍,研究生葛健、郄朝辉,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冯珑珑及朱镇熹,在羊八井观测站主持了平台在高原地区的第一次点火,并成功启动2号发动机为仪器供电。
去年国庆前夕,研究院赴藏人员主要任务是把完成高原综合测试后的平台拆卸装箱,运回南京。但是放心不下的郝英立还是丢下手中正在修改的博士生论文和其他工作,和研究院邱实老师于9月25日从南京启程赶赴西藏羊八井。他觉得这个收尾环节很重要,作为项目负责人应当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什么都考虑得很详细,唯独没有注意到自己正面临着高原缺氧所带来的严重威胁。2010年9月27日,郝英立不幸由于剧烈的高原反应而因公牺牲。当校党委副书记左惟闻听噩耗,陪同郝英立的家属赶到羊八井时,郝英立早已停止了呼吸。
颠簸摇摆中的万里航程
“南极冰穹A科考支撑平台”是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必须将它拆散后运输,并在昆仑站完成组装。项目组根据成员的工作特点和身体条件,决定委派负责平台控制系统设计的自动化学院副院长魏海坤教授作为现场执行人,远赴南极完成平台的安装、调试任务。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安排下,魏海坤和备选成员、电气工程学院金龙教授一起来到西藏,参加奔赴南极前的适应性训练。由于能到南极去的名额实在有限,魏海坤必须要承担起平台组装、调试等所有工作任务。为此,他加班加点研究和熟悉“南极冰穹A科考支撑平台”的每一个零部件、每一个安装环节。经过努力,对于厘米厚的安装程序他牢记在心。但在他心里,一直有一个隐忧,平台能承担起遥远路途的颠簸、完好地到达南极吗?魏海坤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尽管在平台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到运输过程中的抗振问题,但平台要经过几个周转环节,才能到达目的地。它要随雪龙号考察船远赴一万一千多公里外的中山站,并再换乘雪橇到1300多公里之外的昆仑站。在这中间,平台会遇到多少险境、多少困难,没有一点南极经验的魏海坤心里没底。
2010年11月初,魏海坤教授带着一丝担心,与平台一起,随“雪龙号”科学考察船奔赴南极。南极大陆是最难接近的大陆,其冰架和浮冰面积也有260万平方公里;南极大陆周围海洋中还漂浮着数以万计的巨大的冰山,为海上航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危险。因此,一路上,魏海坤无暇顾及从赤道到南极的美丽风光,时常下到舱底,查看平台能否经受住万里航程的考验。
“雪龙号”在海上一走就是近一个月。11月24日,“雪龙号”离开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锚地以后,在穿越南大洋西风带过程中,先后遭遇到6个较大的气旋。根据先进的卫星云图和气象预报,“雪龙”号通过航线的合理安排,有效进行了规避。其中,重点避开了10米高的大浪海域,将船的摇摆幅度控制在30度以内。
虽然现代高科技已经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远航的风险,但“横跨”西风带的那几天,剧烈的颠簸让魏海坤至今记忆犹新。位于南纬45度至60度之间的西风带,素有“魔鬼西风带”之称。强烈的气旋让西风带海域波涛汹涌,排水量2万吨的“雪龙号”像是一叶小舟在海上剧烈的颠簸摇摆中艰难航行。“船颠簸得很厉害,很多人感到恶心,最严重的就靠挂水支撑。我们只能躺着,人只要竖着就想吐。”船晃得最厉害的一次,许多睡觉的人都从床上掉了下来,房间里的物品也被甩了出去,乒乒乓乓散落一地。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魏海坤最为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担心历经千辛万苦,甚至付出战友生命代价的“南极冰穹A科考支撑平台”路途中受到不可修复的损害。
到达南极冰盖最高点
12月4日,饱经风浪考验的“雪龙”号极地科学考察船终于到达南极。由于浮冰太厚,“雪龙”号无法破冰前进到中山站,只能停泊在距离中山站大约30公里的“陆缘冰”地带。
12月5日,包括魏海坤在内的内陆队员乘坐直升机到达了中山站,并立即投入紧张的出发准备工作。一到南极,魏海坤就尝到了南极太阳的厉害。在户外必须戴墨镜,否则很容易会得雪盲症。紫外线也十分强烈,所有人都是6日一天下来脸全变红色,7日变紫色,8日开始脸和嘴唇开始掉皮。特别是嘴唇,不仅掉皮,还开裂,吃东西是没法碰到嘴唇的,否则很疼。抹再多的唇膏和防晒霜都没有用。
雪龙船上的第27次南极考察队员共150多人,但到昆仑站的内陆队只有16人,魏海坤属于其中的5个科学家之一。内陆队总是历次南极科考队中规模最小、风险最大、条件最艰苦、任务也最艰巨的一个队。说风险最大,是因为内陆队的工作地点昆仑站位于南极内陆,是南极冰盖的最高点。从出发地往昆仑站的近1300公里征程中,如果离开中山站200公里,直升机无法救援,一旦身体或车辆出了问题,及时救援基本是不可能的。说条件最艰苦,是因为南极内陆温度极低、极干燥,昆仑站一月份最暖和,温度也在零下400C左右,昆仑站冰芯房的平时工作温度甚至在零下500C以下。而且从出发到返回中山站的近两个月时间内无法洗头洗澡,连洗手都是奢侈。饮食也比较单调,航空餐是路上唯一的选择。说任务最艰巨,是因为上昆仑站不容易,你得在昆仑站15-20天的时间里完成你自己的科研或建站任务。
内陆队使用了6辆雪地车,带着21个雪橇。其中9个是油橇,6个是生活用橇,其他6个橇全是昆仑站的科考物资和建站物资,其中天文的物资,包括平台的两个舱在内,一共占了约2个橇。让魏海坤高兴的是,“南极冰穹A科考支撑平台”的发电舱与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的舱一起放在了唯一的一个减振雪橇上。科考物资和建站物资才6个橇,上其他橇全是为了这6个橇,可见上一次昆仑站做科研要多大代价!
12月17日是出发的日子。随着领队一声令下,六辆雪地车顺次出发。雪地车的速度不快,时速也就十一二公里。从中山站到昆仑站共1260公里,按这个速度,相当于骑自行车从上海到北京。但考虑到路上有不断的陷车、车辆故障、中途加油等因素,按以前的经验,每天也就走80公里。这1000多公里以前历次内陆队通常走十七八天。
从中山站向内陆最要命的是怕遭遇冰裂隙、雪坎、白化天和地吹雪。冰裂隙是指冰层受应力作用形成的裂隙;雪坎是积雪形成的,又硬又高,有的甚至接近2米。能见度不好的时候,每一次急刹车对于雪地车都是致命一击;另一种可怕是遇到“白化天”,天空中白蒙蒙的一片,可以把整个车队“吞没”。完全找不到方向,能见度只有3-5米。后面的车只能跟着前一辆车的车辙向前挪,稍慢一步,车辙被大风吹散,就难免掉队;地吹雪好像北方的沙尘暴,雪落到地上以后,也不会像国内的雪就积起来,而是被狂风再次卷扬到天空中。
由于此前的培训,魏海坤对一路上会遇到的车辆故障、陷车、冰裂隙、雪坎、地吹雪、白化天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幸运的是,除了自己在中山站出发准备阶段偶遇不深的冰裂隙和刚出发几天遇到的地吹雪,随着越走越远,天气越来越好。而且除了出发第三天里一辆雪地车出现了机械故障,其他车辆一直很正常,在前10天几乎没有陷车,白化天,冰裂隙连影子都没见到!同开一个车的内陆队夏立明队长也很纳闷,他直喊今年情况罕见!由于天气好,路况好,停车时间少,车队每天平均开110公里以上。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12月29日下午3:20,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内陆考察队顺利到达了DomeA,海拔4093米的南极冰盖最高点。车队没有停车,直奔7公里外的昆仑站。在昆仑站,经过仔细检查,除仪器舱部分线缆破损外,发电舱安然无恙。魏海坤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从中山站到昆仑站路程,原来是魏海坤最担心的,因为他特别怕平台的两个舱在这段路上受到不可修复的损害,那就意味着项目组30多个人,一年半的工作付诸东流。但今年的雪面特别软,而且发电舱用上了减振雪橇,因此平台的两个舱都安全抵达目的地。魏海坤心里暗想,是否是郝英立教授的在天之灵在保佑着?
坐在南京看南极
在南京时,魏海坤曾经用了两天时间专门演练平台的组装,当时觉得只要按照程序做,不会有较大问题。但是到了南极,在超低温、超低压的冰雪环境下,情况变得相当复杂。队员们穿着厚重的保暖衣、保暖靴,再加上剧烈的高原反应让人时常感觉头疼恶心,走起路摇摇晃晃地像个笨拙的企鹅。因此平时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现在做起来都十分费劲。一米七五的魏海坤本来可轻松搬动百余斤的物件,可到了昆仑站能搬动的重量要大打折扣。
低温的环境也让零部件,特别是电线变得冷硬无比。为了让电线耐低温,项目组在来之前就定制和使用了许多耐低温线缆,但到了昆仑站后,有的电线还是变成了“铁棍”。魏海坤用电吹风和热风枪,双管齐下对着电线吹。电线稍稍软化些,他尝试拧电线线头,还是太硬,拧不过来。只得继续接着用热风枪吹。接一根超级电容的电线就花了一个上午时间。第一根电线接成了,魏海坤的手、脚早已失去了知觉。就这样,魏海坤从12月30日下午一直忙到1月5日,花费了比平时多出两倍的时间才把平台系统组装完毕。但是系统能否开始运作呢?
1月5日一早,魏海坤怀着紧张的心情尝试着给发电机点火,但是经过数次尝试,忙到下午一点都没有成功。情急之下,他一边不断地尝试点火,一边用暖风机对着发电机吹。到下午两三点钟,太阳光正好能照进发电舱的时候,第一台发电机终于启动了。这时,魏海坤知道,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
正当他高兴地想休息一下,夏队长跑来和他讲,随队的医生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喘不过气,吃不下睡不着,人迅速萎靡下去。这名医生再也撑不下去了。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全体大撤退,这意味着此行所有内陆科考项目前功尽弃;二是请求国际援助,请飞机进来救人,但这一定要快。听到夏队长一席话,魏海坤刚刚高兴的心情一下子凉透了。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请求救援后不到24小时,澳大利亚的飞机就停在昆仑站前。这是第一次有外国人上昆仑站。1月6日夜里,内陆队其他15名队员把高原反应的医生送上了澳大利亚的飞机。大家都明白,以后每个人都将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任务。
经过与队友们的多次安装调试,终于在1月7日实现了双向通信成功:图片等数据传回国内!1月8日,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正式宣布,“南极天文科考支撑平台”安装成功,在昆仑站上开始运行。远在南京的同事陆续收到了魏海坤从昆仑站发回的照片和文字,实现了坐在南极看南京的梦想。当晚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专门播送了这条消息。魏海坤满怀激动的心情说:“我的战友郝英立教授在天之灵可瞑目了。”
此次平台安装借鉴了澳大利亚的经验,同时做了进一步改善。澳大利亚平台单台机组输出功率只有1千瓦,我国单台机组输出功率达1.8千瓦,最多可6台机组并网运行,同时实现了智能控制,保证任何时候都有发电机组在运行,一旦出现故障,将由控制系统自主选择蓄电池供电。魏海坤将平台形容为替天文观测仪器提供“吃喝拉撒”的生命保障系统。它的建设也标志着我国在南极建造天文台的帷幕已经拉开。据悉,我校将会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加大研制力度,为昆仑站搭建一个全新的智能平台。新一代平台不仅输出功率更大,在能源使用上也会加入太阳能元素,改变目前完全依赖常规能源的格局。
3月15日,魏海坤教授从澳大利亚搭乘飞机提前回国。虽然他明显黑了、瘦了,脸上还有晒伤的痕迹。但是,他每当谈起南极,回忆起149天生死考验,依然难掩兴奋。他在南京遥感着万里之外的南极内陆冰盖,南极昆仑站的温度、湿度……一切仍在他的眼前。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憨憨的海豹,可爱的企鹅……坐在南京能“看”到南极,这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随着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凯旋而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