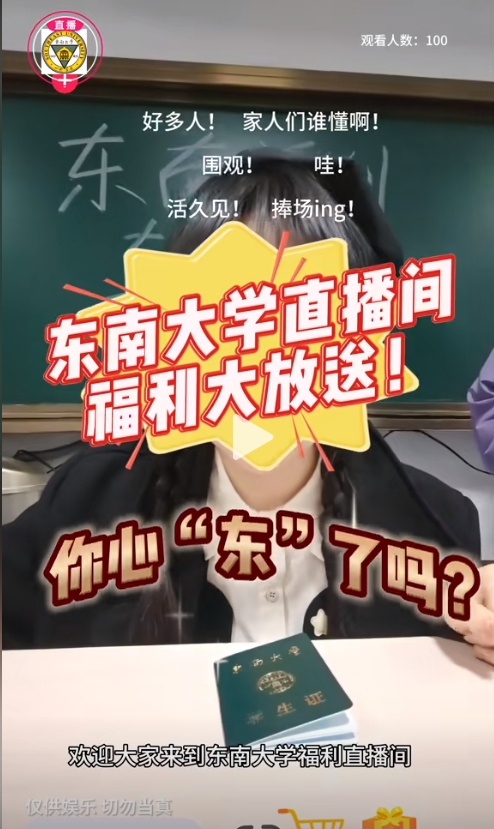“在这样的重大疫情面前,最前端、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医生,而是疾控。如果把第一道防线,比如社区这条线,如果社会的传播能挡住,病人就会变少,重症就会更少”
“经此一疫,我们也应该反思:全国有足够的重症医生、重症护士吗?这是我们的医学教育体制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的培训、毕业后教育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我们在住院医师培训中没有规培(规范化培训)”
文|本刊记者 杨楠 张明萌 实习记者 刘睿睿
编辑|林阆

在日前的采访中,邱海波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有采访过去世患者的家人么?我说有。他问:他们怎么样?我三言两语,简单说了几个。我看到邱海波突然靠着椅背,右手攥了起来,这是人在努力克制自己情绪时的表现。邱医生是个温和的人,在谈及初来武汉时的经历时,他说,有不少可以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
在一月份的武汉,疫情之初,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有力所不能及的无力感,即使你是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点名指派武汉医疗救治专家——这是医生能在此次疫情中所能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之一。
邱海波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副院长,重症医学专家,以下是邱海波的自述:
我1月中旬来武汉,刚来的时候,“新冠”对我来讲是新的疾病,不知道它的特征,需要跟前期当地的医生去聊,病人怎么生病的?需要跟清醒的病人去聊,他有什么不适?对于最重的病人,要看看他现在有哪些器官不好,到底是因为肺,还是别的器官也有问题?当时认为,主要以肺为主,看看该怎么做治疗。那天我是早晨到武汉的,下午就去了金银潭病房。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觉得病人病情较重,第二病人很多,第三是大家好像都有点摸不清头脑,到底应该怎么治不太清楚。
刚开始我们遇到很多困难。一个是没有插管的设备,即使有了,插完管以后,病人到ICU又没有床位,要上呼吸机,一开始呼吸机也不够,医疗资源不到位。当医生看到不少同事感染了,心情可想而知。当时即使有呼吸机,墙上氧气也接不上氧气接口,氧气压力也不够。我们都自己动手搬过钢瓶,我不能让病人憋死了。早期的时候大家都搬,护士搬不动。有什么脏活累活,我们医生先干。我会跟护士说这个事情怎么样,有多大风险,你需要注意什么。要让护士会觉得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医生团队在支撑我们。同时我们也尽快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中央指导组,必须赶紧解决氧气的问题。

邱海波(中)和同事在抗疫一线
早在一月下旬,我们在巡查的时候就发现,病房已经全满了,每天四、五百的门诊量,病人要求住院,但住不进来,没有一张床位是空的。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危重病人在外面等着住院,不知道这些危重病人在外面是不是就这么走掉了。卫健委派我们到汉口的医院去看,一家一家查有多少重病。当时我们查到大量的重症病人,院长们都很焦心,说:我的病人进不来,发热门诊的病人都收不进来,特别重的才能收。如果病情不是特别重,收不进来。当时方舱还都没有,病人只能回家,这些回家的病人里头有多少重症我们不知道。
所以当时我们在卫健委的专家会上,研判疫情,提出要赶紧扩床,收病人进来。一定得去扩重症定点收治医院,就像当年SARS,中日医院、宣武医院征用,全收重症。应该说,这些情况,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得到了改善,我们在短短的三天里面,几乎每天都增加一千张的重症收治床位,不断收治。包括医院的供氧,也都得到了解决。这样的效率,在很多其他国家恐怕是难以复制的。
现在如果说遗憾,早期病人太多,没有足够的床位,没有设备,没有足够的、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这些都是早期非常大的困扰。现在当你去看全球疫情,你会发现,大家都在面临相似的困境。当时金银潭的问题,从我们的角度看,是真正重症医学的医生并不多,但这里的病人是全市最重的。而且你没办法再从协和、同济、省人民这些大医院调增援,因为这些医院自己也有医疗任务。那怎么办?当时我们想,从国家调吧,从国家专家组调,我们希望能调到的是能够带队做医疗组长,能够沉下来的专家。

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邱海波(右)和杜斌结束巡视后顾不上吃午饭,
抓起两片面包就赶往下一家医院 图 / 重症医生晁亚丽
我们的架构大致是这样的:科主任下面,可能有医疗组长,还有主治大夫,再有住院大夫。医疗组长实际上要能够把这组病人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对病人的一切情况负责。我们在临床上真正最了解病情、最负责任的是医疗组长。我们想当时的想法:能不能调一批稍微年轻一点的专家,能够把他放到这些病房里,直接让他去做医疗组长,来保证最重的病人得到专业救治。面对复杂的疫情,光有智商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的情商和综合的能力。
现在还有几百个危重病人,意味着我们还有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工作。有人说觉得我们可以撤了,我们撤不了。我觉得重症病人尤其危重型的病人没有转危为安,没有结局之前,我们都必须坚守在这里。
进入3月份,疫情得到明显控制,ICU开始有空床了,甚至有些医院的ICU都关了,有些医院也不再收治重症病人。病人少了,重症病人也少了,危重病人少了,这就说明我们前面的防护墙起作用了。重症病人比例并不高,但是因为基数太大,重症病人绝对数量是高的。而这么大的绝对数量,就造成了医疗能力的不足,医疗资源不够,而且医疗力量很难整合。
我一直觉得,在这样的重大疫情面前,最前端、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们医生,而是疾控。如果把第一道防线,比如社区这条线,如果社会的传播能挡住,病人就会变少,重症就会更少。
现在疫情已经受到有效的控制,社会比较关心的是复阳问题。其实复阳并不是说没治愈,我们从病理里可以看到,肺里面的细支气管堵住了,肺泡塌掉了,现在已经康复了,够出院标准,可以出院了,也有抗体了。但是在病人的恢复期,支气管又慢慢通了,通了之后里头的病毒就又能排出来,检测就还会再次显示阳性,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观察到复阳的病人有传染性。
经此一疫,我们也应该反思:全国有足够的重症医生、重症护士吗?这是我们的医学教育体制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的培训、毕业后教育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我们的重症医学是二级学科,很多欧洲国家、新加坡、澳洲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跟新加坡、澳洲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我们在住院医师培训中没有规培(规范化培训)的。我们是唯一在二级学科里没有住院医生规培的国家,这意味着我们的住院医生都没有经过重症医学的规范化的培训。
现在年轻的ICU医生、住院医师的规培,都是由其他学科承担的,未必有牢靠的重症医学基础。我们就靠现在重症医学金字塔塔尖上的这一小批重症医学医生,一旦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是承担不了的。但如果我们有了住院医师的规培,即使这些医师在规培之后,可能分化去呼吸科、心脏科、肾科……但是他具备了应对重症的基础,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这些人征召过来,就像预备役部队一样,马上就可以应对紧急情况。我们当然不希望再来一次这样的疫情,但没人能打包票,是吧?
重症医生的作用在哪?当我们有这么多重症病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来面对它?我们一直说,重症医学是生命最后的防线,而重症导致的死亡病例,恰恰是社会最关注的,跟老百姓关系最大的,所以这条防线非常重要。